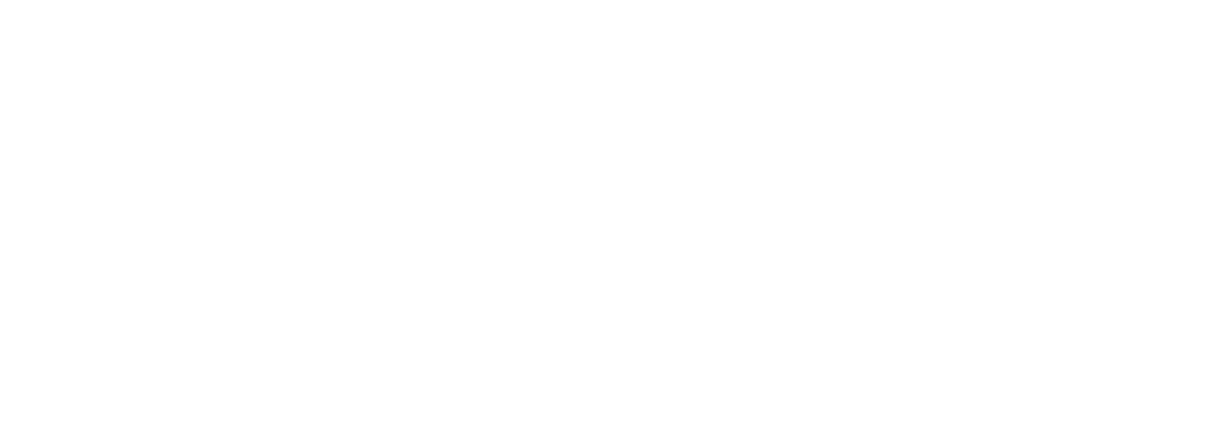| 「職場遊戲規則正在改寫。」Luis Garicano教授直言,人工智能(AI)取代了大量重複性工作,卻也因此減少了職場新人的培訓機會。而企業層面,AI的出現更迫切企業重新審視投資回報和組織管理方式。《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獨家專訪香港大學AI管理與組織研究中心學術顧問委員及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公共政策教授Luis Garicano,預測AI最終會對經濟帶來的深刻改變。——撰文 楊瀅瑋;編輯 鄧詠筠 |
| AI會如何改變初級員工的職業生涯,而年輕人又要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呢? 貝克(Gary Becker)曾經提出一個理論,指公司考慮到競爭對手的挖角而不願投資在員工的基礎培訓。因此,律師事務所、投行或顧問公司會設置初級員工崗位,讓他們負責審核文件等瑣碎工作來「支付」專業訓練的學費。而現在,AI幾秒鐘就能完成這些文書任務,行業規則便被改寫了 — — 初級職位在縮減,職業生涯的「首個梯級」正在消失。 在這背景下,我和香港大學兩位教授共同提出了「監督門檻」(supervisory threshold)的概念,即能否在特定知識領域上監督AI生產的內容,通過檢查、驗證和改進AI來創造價值。 要達到門檻,有兩種能力非常重要:豐富知識(substantial knowledge),即專業領域的基本框架與事實;以及AI工具的使用經驗。隨著AI進步,這個門檻將會越來越高,而無法達到門檻的人會被AI取代。 所以,高等教育也要往兩方面改革。大學應該「倒退」,更強調基礎課,甚至回到傳統的紙筆考試和一對一討論,確保學生真正理解基本理論和模型,培養判斷力。另一方面,在高年級課程中,AI必須成為「必修工具」。我會要求學生利用AI做出比以往好十倍的成本效益分析,而非用它來節省時間,做出跟以前一樣的成果。 AI會否進一步拉闊高技能與低技能職位之間的差距? 從宏觀數據來看,我們確實看到程式員等入門崗位在減少,而頂尖AI工程師的薪資卻屢創新高。但最近一份關於客戶服務行業的研究卻顯示了另一面:AI 幫助初級客服學會如何表達和溝通,反而縮小了他們與資深客服的差距。關鍵在於AI 的使用模式,後者屬於「協作型 AI」,能成為職場新人的「副駕駛」(copilot),幫助新人更快成長。 雖然很多企業都在投資AI,但也有高層抱怨回報率並不理想。你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許多回報都被員工「吃掉了」。我認識一些在中央銀行的職員,出於保密要求,他們並不能使用AI,但他們也會偷偷用自己的電腦運行ChatGPT完成文書工作。所以,企業必須要重新圍繞AI的組織工作流程和激勵機制,例如建立跨部門的數據協作機制,增加績效浮動的薪酬設計,才能讓AI的價值顯現出來。 其實,企業不應該急於追求短期投資回報。ChatGPT出現才兩年,技術和應用模式還在摸索期。其次,投資重點應轉向數據和人才。除了數據和專業知識,所有東西都能被商品化。 如果未來是AI主導工作的話,那意味著工作模式將會變成一位專家來指導許多AI機械人和模型去完成工作,那投資在數據和人力資本才會帶來真正的回報。 AI未來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方式會是怎麼樣的,是會提高生產效率,還是會創造出新的行業? 歷史上,很多突破性創新並沒有直接推高GDP,例如電燈的出現,讓照明幾乎免費化,但蠟燭這個產業卻消失了,GDP貢獻反而下降。但突破性的創新會帶來大量的「消費者盈餘」(consumer surplus)。有一個經濟學概念叫「鮑莫爾效應」(Baumol Effect)。17世紀和20世紀的音樂家演奏同一首曲子,生產力並沒有提升,但後者會因為社會成本提升而提升價格,從而提升收入。我認為AI 可能會重演這個故事,即可以通過AI自動化的行業將會逐漸飽和而效益降低,而經濟中未實現自動化的部分,經濟效益會被動提升,GDP佔比也提升。短期來看,技術最初帶來的仍是替代效應,AI自動化會取代掉重複性工作,也會創造出新的崗位。但風險是,變革可能會發生得太快 — — 當我們透過自動化獲得大量生產力和消費者盈餘,卻沒有來得及創造新工作,社會就會陷入動蕩。 |